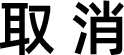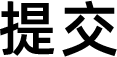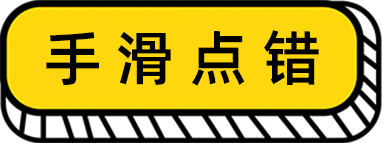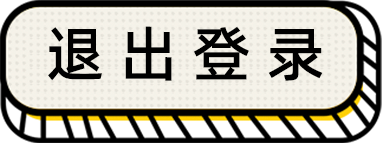明清时期,水仙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,除浙、闽、鄂、湘外,皖、赣、黔、川、滇、桂、琼等地志乘中都有了关于水仙的记载。如《(嘉靖)广德州志》(今属安徽宣城市)、《(嘉靖)南安府志》(治今江西省大庾县)、《(嘉靖)普安州志》(治今贵州省盘县)、《(嘉靖)洪雅县志》(今属四川眉山市)、《(万历)雷州府志》、《(康熙)云南府志》、《(乾隆)广西府志》物产中都著录有水仙。
江苏南部的水仙种植有了明显的发展,形成了一些著名产地,出现了不少优良品种。嘉靖王世懋《学圃杂疏》称“凡花重台者为贵,水仙以单瓣者为贵。出嘉定短叶高花,最佳种”。万历于若瀛《金陵花品咏》水仙序也说“水仙江南处处有之,惟吴中嘉定种为最,花簇叶上,他种则隐叶内”,都是说产于嘉定(即嘉定县,明代属苏州府,今属上海市)的水仙单永承奔瓣、短叶、高花,品种优质。万历兵设欠周文华《汝南圃史》“吴中水仙唯嘉定、上海、江阴诸邑最盛”,也可印证。除以上所说几个盛产水仙的地区外,吴县(今江苏苏州)也出产水仙,该县水仙主要出自“光福(引者按:今吴中区光福镇)沿太湖处”。查阅明代苏州方志,《(正德)姑苏志》、《(嘉靖)吴江县志》、《(嘉靖)太仓州志》物产中也都著录有水仙。种种迹象表明,明代嘉靖以来,苏州嘉定、吴县一带成了水仙种植的中心地区,影响很大。此外,杭州海宁县钱山也以出产水仙著称,曹学佺《杭州府志胜》载“钱山,产水仙花”。明末北京还出现了水仙的繁殖基地和贸易,崇祯刘侗等《帝京景物略》“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”,“居人遂花而生。入春而梅,而山茶,而水仙”,都说明了明代水仙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化的发展。
苏州水仙种植兴盛,声名远播,在清代进一步市场化,销往广东,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年间。乾隆毕沅《水仙》诗注:“邓尉山(引者按:位于今吴中区光福镇)西村名熨斗柄,土人多种水仙为业。”清初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载“水仙头,(引者按:鳞茎)秋尽从吴门而至,……隔岁则不再花,必岁岁买之”。乾隆张九钺《沁园春·耿湘门以水仙见贻》注:“水仙自吴门或飘海或度岭来羊城。”说的都是苏州水仙贸易到广东的情形。而此时金陵(今江苏南京)的水仙也开始兴盛。清初李渔《闲情偶寄》:“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,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权,欲其早则早,命之迟则迟。……买就之时给盆与石而使之种”,说的就是金陵水仙的生产和贸易情况。
康熙中后期,水仙种植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福建,漳州水仙异军突起。福建是中国水仙的传统产地,南宋时建阳一线即以盛产水仙著称,明代《(弘治)八闽通志》福宁府、福州府、泉州府物产志中都有水仙的著录,但漳州府并没有著录水仙。我们查阅现存其它明代漳州府及其所辖县志,如《(正德)大明漳州府志》、《(嘉靖)龙溪县志》(1535年刊本)、《(万历)漳州府志》(1573年刊本和1613年刊本)、《(崇祯)海澄县志》(1633年刊本),物产志中都未著录水仙。明末龙溪县学士陈正学在《灌园草木识》中说“漳南冬暖,(水仙花)多不作花”,或许道出了其中的原因。这说明明代漳州有水仙种植,但并不突出。康熙前期,漳州各地的水仙还主要来自江南,《(康熙)漳浦县志》(39年刊本)称“水仙花,土产者亦能着花,然自江南来者特盛”
从康熙中后期开始,漳州府龙溪县水仙开始一枝独秀,产生影响。《(康熙)龙溪县志》(56年刊本)“水仙,岁暮家家互种,土产不给,鬻于苏州”。是说龙溪县水仙种植销售比较兴旺,供不应求。康熙末雍正初出使台湾的黄叔璥在《台海使槎录》写道:“广东市上标写台湾水仙花头,其实非台产也,皆海舶自漳州及苏州转售者,苏州种不及漳州肥大”,可见至迟康熙末年,漳州水仙开始外销,与苏州水仙相媲美,并且形成特色品种,以“鳞茎肥大”著称。到乾隆年间,漳州水仙已超过苏州,《(乾隆)龙溪县志》(27年刊本):“闽中水仙以龙溪为第一,载其根至吴越,冬发花时人争购之。”说明龙溪水仙开始返销长期以水仙著称的吴越地区。漳州与苏州一起,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水仙产地,并且有过之无不及。乾隆以来,与漳州府相邻的泉州府各县以及台湾、广东等地每年都从漳州贩购水仙花头。如泉州府属的马巷厅,《(乾隆)马巷厅志》载“水仙花……不留种,花时取诸漳郡”,台湾《(光绪)恒春县志》记载“水仙皆产自闽漳州,他处不能种焉,故只供玩一春”。乾隆以后,漳州成了全国水仙种植、贸易和出口的主要地区。从光绪年间开始,漳州水仙不仅经销国内,还自厦门出口远销至美国、加拿大等海外地区,由此漳州成了国内最著名的水仙产地。宣统三年(1912)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称:“水仙球茎种植于两山靠近漳州城的南门,当地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出口到美国、加拿大的水仙球茎贸易。”(厦门海关《年度贸易报告》)